海德格尔明确表示:“事物存在;人类、礼物、祭品存在;动物和植物存在;用具和产品存在。”相反,某物之所是,以及我们如何领会它,都是某种总是已经通过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被去蔽的东西。语言以及其他形式的介质,或者通常被称为“表达工具”的那些东西,都不应该被看成现实事物组成的既有世界的苍白反映。或者说,这些研究领域不应当把表象视为那个被表象的“第一性”现实的衍生物。......
2023-10-30
在门被堵死之时,思想之不被干扰就变得愈加重要了。
[Adorno,1991(1969):200]
也许,唯一可行的姿态就是等待。人们将自身付诸等待……人们等待着,而这种等待,尽管难以言明,却是一种尚有踌躇之意的开放姿态。
[Kracauer,1995(1963):138]
结论部分的标题概括了我们对海德格尔对当代文化理论的贡献的解读。德里达指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齐泽克亦主张,意识形态是社会条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与此相仿,海德格尔思想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正是在面对无可隐瞒的必然性时,我们才最需要对物提出迫切的追问。有鉴于此,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并不会给出什么答案。在那些热爱新兴事物的评论者看来,媒介的每一步发展都有着令人兴奋的无限可能,都有助于人类获得解放。但海德格尔却不愿意像这些人一样兴奋,他劝说我们后退一步,以便看清技术的本质。在这个时代,对抽象思考的方法形成围攻之势的,正是那些适合在媒介上展示的金玉良言,是140字的推特消息,是那种以非反思性的、乐见的态度为技术背书的总体氛围。在这种情况下,海德格尔坚定的存在论路径不仅与阿多诺对思想不受打扰之强调保持一致,而且还能够对克拉考尔所说的那种难以言明的、“尚有踌躇之意的开放姿态”作出回应。
人们要看清以下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方面,某种情境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这种不可避免性意味着不值得对那种情境进行思考。同理,本书通篇在告诉我们,尽管技术确实已经四处扩散开来,无所不在,尽管技术已经成为人们体验世界的方式的本质性要素,但是,如果我们接下来得出结论说,技术无非是一种使我们得以与事物照面的中性中介,那么我们就在观念的层面犯了错误。技术条件也许确实是无可摆脱的,但这并没有免除我们认识这一事实的责任,我们仍然要思考它的意义。我们与技术之间的关联是持续发展的,对于这种关联的本质,我们仍然要在保持开放心态的同时持批判态度。这就是说,一种无可回避的存在论条件,并不同于不可避免的现象学事实。
为了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方法保持一致,本书各章都在强调应对那形塑存在之揭示的结构进行反思,而不应仅对存在者的个别显现进行反思。我们一直在说明如何从海德格尔的视角全面理解媒介发挥中介作用的方式;人们应当理解某种中介与其所处的更宽广环境之间的关联。本书各章对这一更宽广环境的多种面向进行了解读。
1.语言是一种元—中介,它不仅事关我们如何言说,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事关我们如何被言说。
2.正确性与真理是不同的——通常,占优势的是表象的正确性,而不是真理的揭示。
3.作为存在者的事物存在于更宽广的环境中——这个环境有多大,我们对现实的经验被先行对象化的程度就有多大。
4.以上这些因素都借助技术的构造性而最终发挥效用——技术构造背景,使事物得以显现。
现在来看语言和真理方面。本书使用了诸如“关于本质的本质问题”和“以技术的视角考察技术”这样的表述。这样做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希望模仿海德格尔的表述方式。海德格尔尝试实现对技术的真正领会,而他所用的方式就是:借助语言创造足够的反思性距离,远离技术过程,从而避免以非反思的方式被技术过程所改变。而我们使用那种明显带有同义反复特点的表述,无非是在直接尝试传达这种海德格尔式的意涵。因为我们知道海德格尔使用那些抽象的表述的原因,所以在解读这些表述时,我们并没有被其抽象性吓退,并且,我们发现海德格尔的分析方式对于理解当今媒介那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是非常有用的。这种分析方式之所以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就在于它有助于我们超越对任何特定的装置或通信设备的个案研究,超越那个最具误导性的观念——技术具有中性本质。
在此前的各章中,我们一直在解释以发挥中介作用为基础的媒介技术为何会时常被错误地视为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的中性工具。即便是像媒介与传播研究这种本应具备更强实力去对技术那极其微妙的本性进行全面反思的学科,也仍然持有这种错误观点。海德格尔借助对技术的追问对那些根本性假设进行不懈考察,以便在观念层面实现突破并远离传统的研究路径。最重要的是,海德格尔的路径并没有聚焦于各种单个的技术工具的性质,而是把我们引向对什么构成了工具性本身这个问题的追问。这种关注抽象内容的意图容易被人们误读成某种完全不可理解的、非实用主义的思想。但是,海德格尔的思想无论如何都不是某种只与非现实世界相关的抽象。事实上,他的思想应该被正确地理解为对抽象性与特殊性之间关联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恰恰能够让物( )与实用性关联起来。[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自诩为实用主义者的人在实用主义方面还比不上海德格尔。
)与实用性关联起来。[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自诩为实用主义者的人在实用主义方面还比不上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的著作启发我们去挑战那些宣称媒介具有中性本质的明显不完整的解(误)读。这种挑战可以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程式来概括。我们能够充分意识到,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些等式不可避免地构成了我们之前质疑过的“计算复合体”的一部分。不过,尽管如此,这三个方程式仍然是有帮助的。本书前边的章节考察的是海德格尔在技术裹挟现代形而上学方面的不懈追问,而以下三个方程式的作用就在于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明确并归纳这些追问中的关键因素及内涵。(www.chuimin.cn)
方程式1
t=r=m
从工具主义和人类学层面理解的技术(t)等同于,或至少在本质上类似于被海德格尔称为“上手之物”的东西(r)——《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上手之物”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分析。技术和上手之物都被理解成“服务于人的特定目的的工具”,因此从字面意义上看,这两者都是媒介(m),都是工具或介质。这就意味着,对海德格尔来说,任何东西本质上都是媒介,并且,正像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著作那样,对“媒介”的这种概念化是宽泛而抽象的,它涵盖了“人类的延展物”的各个方面。不过,麦克卢汉只是把“延展物”理解成加之于人类机能上的附属物或假肢。而对海德格尔来说,“延展物”则是此在总是已经被抛入或被拉入操劳打交道之中的方式,而技术对象正是在这种操劳中被使用并与人照面的。
“媒介性”(the media)[2]因而并不是一种以上手之物的形式存在于诸事物之中的技术对象或对象复合体。相反,它构成了技术对象本身与人们照面的存在论结构。因此,海德格尔的著作在帮助我们理解“媒介性”之泛在性本质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海德格尔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分析“媒介性”。海德格尔的不懈追问并不是一种深奥的、极其形而上学的、与前沿媒介技术无关的东西(不过,传播研究似乎通常恰恰将海德格尔著作视作这种东西)。海德格尔的这种追问所涉及的存在的概念无疑是抽象的,并且这种追问看起来与媒介不相关。但事实上,理解媒介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追问。海德格尔的理论可以让我们洞察那些有时离我们太近以至于我们无法明察的问题——麦克卢汉所说的生活在水中但不了解水的鱼,以及齐泽克在《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Žižek,2006b)中描述的视角转换,都涉及此类问题。
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作为万事万物的媒介(或者用更合适的提法:联结起万事万物之存在的媒介)构成了事物的总体条件——更准确地说,构成了所有那些作为对象被我们认识并与我们照面的事物的总体条件。这意味着:
方程式2
t≠T
在对技术(t)的传统理解中,技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器物和工具与我们互动的东西。这种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准确的;在他看来,这种理解与我们平时对技术的显现方式的认识和体验相符,与技术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我们评价技术的方式相符。对技术的这种理解构成了一个有效的起点。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对技术的工具性界定在我们人类阐释技术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工具性的作用。尽管这种界定是正确的(或者,按照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洞穴寓言”的解读,这种界定是 ),但是它并不必然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这种理解并不能在本质层面解蔽(
),但是它并不必然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这种理解并不能在本质层面解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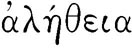 )技术的本质(用T表示)。因此,以标准的工具主义和人类学方式来理解技术(t)——就第一个方程式而言,不仅是技术(t),而且还有媒介(m)——并不等同于技术的本质(T)。将技术理解成人类的行动和卷入关联的工具固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以此方式理解的技术与技术的真正本质有着显著差异——海德格尔提醒我们说,技术的本质“绝不是任何技术性的东西”。这就留下了一个重要问题:T是什么,技术的本质是什么?
)技术的本质(用T表示)。因此,以标准的工具主义和人类学方式来理解技术(t)——就第一个方程式而言,不仅是技术(t),而且还有媒介(m)——并不等同于技术的本质(T)。将技术理解成人类的行动和卷入关联的工具固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以此方式理解的技术与技术的真正本质有着显著差异——海德格尔提醒我们说,技术的本质“绝不是任何技术性的东西”。这就留下了一个重要问题:T是什么,技术的本质是什么?
方程式3
T=τ+λ
理解技术的本质(T)的重要意义可以从词源学上找到。“技术”(technology)是由两个希腊文单词组成的复合词,这两个单词是“技艺”[ (techne)]和“逻各斯”(
(techne)]和“逻各斯”( )。后者代表的是语言的本原层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其称为言谈或话语。因此,我们可以说,技术的本质(T)可以从技艺(τ)和逻各斯(λ)所表达的整体含义中找到。“技术”一词意味着,作为语言的本原而开启了存在者之存在的逻各斯,被要求与技艺相适应,受技艺规制。而技艺不仅意指基于技术性技巧(technical arts)的制作而且还指这种技术中的技巧(art of such technique)本身。
)。后者代表的是语言的本原层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其称为言谈或话语。因此,我们可以说,技术的本质(T)可以从技艺(τ)和逻各斯(λ)所表达的整体含义中找到。“技术”一词意味着,作为语言的本原而开启了存在者之存在的逻各斯,被要求与技艺相适应,受技艺规制。而技艺不仅意指基于技术性技巧(technical arts)的制作而且还指这种技术中的技巧(art of such technique)本身。
以这种视角来看,技术对海德格尔来说就不是什么来自某个外在领域的外在威胁。它并非像当代科幻小说所写的那样,显现为从另一个时空袭来的恐怖的机器人或致命机器。相反,技术已经是逻辑或逻各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技术,我们居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在感知和认识中得到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图像)才成为可驾驭的、有用的,才为我们所见。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技术。此处我们应重申那个极具挑战性的德里达式的观点:技术秩序之外别无他物。在技术这种起整合或框定作用的特殊逻辑之外,并无其他空间、位置或立场。因此,最重要的并非是向媒介技术发出最后通牒。这种发出最后通牒的做法,将现代技术世界观对立于某种前现代的乡村田园诗式的浪漫观念。后者看上去是一种最终的、决断性的选择,但它只是表面上如此而已。这种做法不仅代表了错误的二分法,还代表了海德格尔的那些反对者强加于海德格尔身上的轻率选择。在这些反对者看来,海德格尔通过向技术发出最后通牒,来逃避对存在论分析的内涵进行沉思。
有关海德格尔论媒介的文章

海德格尔明确表示:“事物存在;人类、礼物、祭品存在;动物和植物存在;用具和产品存在。”相反,某物之所是,以及我们如何领会它,都是某种总是已经通过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被去蔽的东西。语言以及其他形式的介质,或者通常被称为“表达工具”的那些东西,都不应该被看成现实事物组成的既有世界的苍白反映。或者说,这些研究领域不应当把表象视为那个被表象的“第一性”现实的衍生物。......
2023-10-30

此在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于其他存在者之中的存在者。在标准德文中,Dasein意指“存在”,但是海德格尔则强调使用“在此存在”这个字面意思,以此来表达人类存在所具有的特点。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仅在牵涉与存在相关联的特殊行为方式时才有意义,而存在却与此不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本身无法被体验,存在并不是那种与存在者并列并能与我们照面的另一个存在者。......
2023-10-30

换句话说,人们与事物照面的首要方式,并不是凝视事物的外表以便发现它们之所是。虽然有些研究者本应被视为媒介理论家,但这些研究者的理论却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存在关联。麦克卢汉借此说明,对媒介的自我消费往往以一种无反思的方式被完成。这是因为,某种上手之物被看作、被概念化为中间物或媒介。所有事物,就其是某物而不是虚无而言,全部已经是媒介了。......
2023-10-30

对真理的追问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部伟大著作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从字面意义上看也是如此,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恰好就出现在该书的中间位置并且在该书的第一篇和第二篇之间起着过渡作用。这些新闻报道和媒体给出的其他断言所具有的真理性,最终在进攻伊拉克之时和后续的占领时期被付诸检验。这些游戏节目的产生和运作完全符合海德格尔所说的“真理的相合性理论”。......
2023-10-30

波兹曼对于互联网上的言论背后的真理(或谬误)的追问有助于我们分析媒介中的相合性理论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媒介在塑造我们对相合性理论的理解时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些案例中,录音并不是与现实中的现场表演相合,而是与借助录音技术产生又以录音的形式存在的理想演唱相合。相反,海德格尔所做的就是超越这种预设,进而对真理问题进行追问。......
2023-10-30

换句话说,传播研究认识到传送模型描述了中性的传播过程的理想形式,而这一理想形式又会因日常实践中的各种危机、干扰和封锁而被复杂化。这种行为在海德格尔看来实际上作为衍生物或特例隶属于一种更宽泛的传播形式,而与这种更宽泛的形式相关联的,并不是那种在语言中并借助于语言得以发生的事情,而是存在被表达的特定方式,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话语——话语是一种普遍的揭示形式,而不仅仅是信息传送。......
2023-10-30

谈起媒介,我们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在使用某种形式的媒介。因此,语言被普遍认为是人类传播的第一中介。因此,本章作为全书之开篇理应探讨海德格尔如何借助语言并以媒介的起源为出发点去挑战那些关于媒介的天经地义的假设。对海德格尔来说,语言是人类表达的工具或媒介这一传统观点是有待商榷的;他甚至还与表面上看起来毫无争议的观点背道而驰,因为他认为拥有并使用语言的不仅仅是人类。本书将会反复提及海德格尔的这一特点。......
2023-10-30

最终,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并没有提供给我们预先编造好的答案或者易阐述的解决方案。相反,海德格尔以更谨慎的方式构造并阐释了他的结论。因此,海德格尔并没有回答关于技术的任何问题。正是这一深层原因使得海德格尔并没有天真地信赖艺术的救赎力量。因此,海德格尔用以结束《技术的追问》一文的并不是某个答案,而是“追问是思想的虔诚”这句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德格尔恰恰是以实用性为起点来进行思考的。......
2023-10-3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