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级行政区的图经编纂和地图的绘制,唐朝政府已有明确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朝廷定期编绘全国性的地图。唐代疆域辽阔,中原与边疆地区、唐朝与境外各国间的往来交流极其频繁,因而比较注意地理资料的积累和地图的编绘。有机会到外国的使臣、将领,巡视边疆地区的官员还主动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绘成地图。......
2023-11-30
三、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地图
(一)形形色色的地图
到了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的汉代,地图的绘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地图的运用更加普遍,并且出现了各种类型、各种用途的地图。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淮南王刘安向武帝建议不要进攻闽越时曾说:“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在地图上观察闽越国的山川要塞,相差不过一寸多,但实际上的距离有数百上千里。)这应该是一种画着地形和军事设施的小比例尺地图。元朔六年(前123年),淮南王企图起兵叛乱,与谋臣左吴等按照“舆地图”,日夜不停地部署兵力和行军路线。“舆”是记载非常详细的意思,可见这种舆地图比例尺相当大、内容也相当详细。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武帝时,张骞及其率领的使者从西域归来,向武帝报告了他们“穷河源”(一直追踪到黄河的发源地。实际是误以今新疆塔里木河为黄河的上源),发现黄河发源于于阗,并且带回了当地山上采来的玉石。汉武帝“案古图书”(查考了古代的图书),将黄河发源的山命名为昆仑。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图书”,并不是我们今天对书籍的通称,因为古代的“图”与“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图”就是地图,这说明西汉时还保存着的古代地图已经包括今新疆的范围,并且绘出了当地的山川。
汉武帝太始年间(前96—前93年),有一个名延年的人上书道:“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流经中国,注入渤海,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可以根据地图和资料,考察地形,命令水利工程师量出高度的差别,将黄河引过分水岭,使河水流经匈奴地区,再东流入海。)延年的建议说明当时的地图不仅已包括黄河上游和今新疆境内的昆仑山,而且可以看出地势的高低。
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受命治理黄河,汉明帝在召见后,特意赐给他《山海经》、《河渠书》和《禹贡图》。虽然我们无法肯定《山海经》和《河渠书》中是否附有地图(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但《禹贡图》的名称就明白无误地说明,这是一幅或多幅描绘《禹贡》一书有关内容的地图,而《禹贡》的内容包括黄河及其支流,有关的山脉、山峰、城邑、物产、土壤、植被等许多方面。
东汉初年还出现了立体地图的雏形。建武八年(32年),汉光武帝将要出征隗嚣,马援在他面前“聚米为山谷,指划形势”(用米堆成山谷的形状,讲解敌我双方形势),光武帝听后连声称赞,说:“虏在吾目中矣。”(敌军都已在我眼中了。)大概这种以米垒成的立体地图是相当直观的。
由于绘制地图的技术已比较普及,文武官员往往随时随地绘成新的地图,作为行军作战或治理开发的工具。朝廷也经常命令有关官员绘制新的地图,以适应军事或行政的需要。
如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汉将李陵率步兵5000人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北行30日,到达浚稽山(约在今蒙古国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以南一带)。李陵将所经过的山川地形画成地图,派部下骑士陈步乐上报武帝,使武帝非常满意。
征和四年(前89年)治粟都尉桑弘羊和丞相御史向武帝建议: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以东的捷枝、渠犁有5000顷以上的土地可以开垦,可以调遣戍卒去实行屯田。可以设立三个校尉官分别负责,要求他们“图举地形”,开发水利,及时扩大五谷的种植。看来,这些校尉在勘察地形的同时,负有绘制成地图上报之责。尽管这一建议被武帝否决而未能实行,但证明这是文武官员一项正常的职责。
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张千秋和大将军霍光的儿子霍禹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征乌桓(今内蒙古东南和辽宁西北一带的少数民族)。回来后,霍光召见张千秋,问他战斗方略和山川形势,张千秋边说军事形势,边在地上画成地图,一点没有遗忘。但问霍禹时,他却记不清楚,回答说:“都已有文书记录了。”张千秋能随手画成地图,固然与他记忆力强有关,但也证明了当时地图应用的普及。或许霍禹所说的“文书”中,也包括了有关人员在行军途中画成的沿途地图,张千秋只是凭记忆重画而已。
东汉章帝(75—88年在位)时,侍御史李恂奉命巡视幽州(今山西东部、河北、辽宁一带),在北部边疆抚慰少数民族。李恂将所经过地区的山川、屯田、聚落绘成详细的地图百余卷,回京后上奏朝廷,受到章帝的嘉奖,被封为兖州刺史(今山东西部、河南东部一带的监察官)。李恂画的大概是非常详细的分幅地图,所以才会有百卷之多。
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展和与周边少数民族交往的频繁,汉人的地理知识不断增加,所绘制的地图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东汉永元元年(89年),汉将窦宪、耿秉率军大破北匈奴,出塞3000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在山上刻石纪功。由班固所作的《燕然山铭》中写道:“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候,乘燕然。”(我们考查了文献记载,对地图进行了核对,对匈奴的山川早已完全了解,于是翻越涿邪山,跨过安候河,登上燕然山。)这表明,在窦宪出兵前,曾经查考了有关的文字记载和地图,而地图的范围显然已经包括今蒙古国在内的北匈奴地区。《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前111年)“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后人臣瓒作注时写道:“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可见臣瓒看到的《汉舆地图》包括远离汉朝边界2000里外的匈奴地名,并且不排除在图上注有里程的可能性。
另一类是主要描绘疆域、政区的地图。
当时的一级行政区域郡、国是地图上的基本内容,所以查阅地图后就能知道全国郡、国的情况。更始元年(23年),刘秀在河北起兵时,邓禹曾对他说:“夺取天下不会有什么困难。”第二年,刘秀在广阿县(今河北隆尧县东)城楼上查阅地图,发现自己占有的地方很少,就责问邓禹道:“天下郡国这么多,如今我才得了其中的一个,你上次却说夺取天下不会有问题,有什么道理?”以后隗嚣割据陇西时,马援曾劝说他的部将杨广说:“我不久前刚查了地图,天下的郡、国有106个,为什么要以区区两个郡与中原104个郡国对抗呢?”
汉朝封诸侯王时,都要由有关部门呈上地图,由皇帝确定王国的范围和名称。如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四月,御史奏上“舆地图”,请皇帝确定国名。10天后,正式立皇子刘闳为齐王、刘旦为燕王,估计已在地图上画出新王国的范围和国名。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光武帝分封皇子,也是由有关官员奏上地图后才正式进行的。
郡一级的政区图可以精确到乡一级的界线和乡以下的地名,并且不断修订。临淮郡的僮县(今安徽泗县东北)有个乐安乡,有田3100顷,南面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前48年)修订郡图时,误将乐安乡的南界画到了平陵佰,使该乡多了400顷田。丞相匡衡被封为乐安侯,乐安乡成了他的食邑,就多收了400顷田的租米。到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郡里勘定乐安侯国的界线,才发现图上的错误,就作了更正,上报丞相府。匡衡身为丞相,却示意属官以旧地图为依据,向临淮郡提出质问,使郡太守不得不将错就错,将400顷田划给乐安侯国,使匡衡多收了租谷千余石。这两次修订郡图正好相隔10年,可能是当时规定的年限。
在相邻的政区为分界线发生争执时,地图往往能起到权威的裁决作用。三国魏时,清河、平原二郡的边界纠纷闹了八年,它们的上司冀州刺史换了两任都没有能解决问题。孙礼出任刺史时,太傅司马懿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烈祖(魏明帝)初封平原王时画有地图,现在藏在皇宫,只要拿这张图一查就可以确定。”查了原图后,证明双方有争议的土地在高唐县西北,应该属于平原郡。
这类地图上还记录着租税、户口等数据。永平十五年(72年)汉明帝封诸皇子时,先在地图上审定范围,都只及已有王国的一半。马皇后在旁边见了,说:“孩子们只有几个县的租税,照制度是不是太少了些?”明帝说:“我的儿子岂能与先帝的儿子一样?每年有2000万石租米收入就足够了。”建初四年(79年),章帝亲自修改“舆地图”,将他的兄弟广平王、钜鹿王、乐成王等的封地都增加到每年可以收入8000万石租税的范围。
此外,还有城市图和宫殿图。如著名的《三辅黄图》详尽地记载了汉代以长安为中心的三辅地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直属中央的政区)内的宫殿、陵墓、寺庙等建筑和城市布局,本来是有图的,只是以后失传了。无论是单幅还是多幅,这就是西汉首都地区的城市图和宫殿图。西汉时还有一种《长安图》,原图虽已无法看到,但从后人的引证中还可以作些推测。如《史记·文帝纪》裴骃〔yīn因〕注引如淳说:“《长安图》,细柳仓在渭北,近石徼。”《文选·西征赋》注引《长安图》:“汉时七里渠有饮马桥。”可见《长安图》既包括城内,也包括城郊,至少标注着水渠、桥梁、仓库及其他地名。此外还有《关中图》、《雍州图》等,如《续汉书·郡国志》注:“案《关中图》,县南有新丰原。”
三国时出现过一种以刺绣制成的地图,据《拾遗记》记载:
孙权常叹魏、蜀未灭,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于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
〔今译〕孙权经常感叹没有消灭魏、蜀,在军旅的间隙,想物色一位善于画图的人,让他将山川、地势和军阵布置画成地图。(赵)达推荐了他的妹妹,孙权就让她画出九州的江湖山岳的分布。(赵氏)夫人说:“用颜色画很容易褪色,不能长久保存,我能用刺绣将列国绣在一块方帛上,同时还能绣上五岳、河、海、城邑和行阵的布置。”这幅地图绣成后,就进献给吴主孙权。
这类地图只是用彩色的线代替了绘制地图时的颜色,刚绣成时或许比较鲜艳,日子长了也未必能保持不褪色,不仅制作费时、费钱,而且不易保持精确,所以没有推广的价值。
(二)马王堆汉墓地图
西汉和东汉400多年间的地图是如此丰富,质量也相当高,可是到了3世纪末的西晋初年,裴秀却说:“现在秘书院中既没有古代的地图,又没有萧何所获得的秦朝地图,只有汉朝的舆地图、括地图等杂图,都没有比例尺,又不考察修正相互间的位置关系,连名山大川也不详细记载,虽然有大致的形状,但都不精确可靠,没有办法作为依据。”
作为一位著名的地图学家,裴秀所说当然都是事实。显然,经过东汉末年和三国的战乱,汉朝的地图绝大部分已经不存在,所以裴秀无法看到真正高质量的汉代地图了。所幸保存在地下的西汉地图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2100多年后重见天日,为我们纠正裴秀的误解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地图有三幅,但其中一幅因破损过于严重,难以修复。其余二幅,整理小组分别命名为《地形图》(另一种意见应命名为《长沙国深平防区图》)和《驻军图》。
《地形图》长宽各96厘米,以上方为南,下方为北。制图的区域大致包括东经111度至1125度,北纬23度至26度之间,约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灌阳一线以东,湖南省新田、广东省连县一线以南,北至新田、全州,南达广东珠江口外的南海。地图的主区包括西汉初所封长沙国的南部,即今湘江上游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附近地区。主区的比例尺大致在1∶170000—1∶19000之间,按照当时的长度单位折算,图上的一寸大约相当于实际的十里。图中已有统一的图例,表示的内容有山脉、河流、道路、居民点等(图9)。

图9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形图复原图 (www.chuimin.cn)
《地形图》上山脉的画法特别值得重视,即用闭合曲线并加晕线,表示山脉及其走向,比《放马滩地图》又有了进步。对九嶷山的表示更有独到之处,除了用闭合曲线勾出山体外,还用细线画成鱼鳞状层层重叠,以显示峰峦起伏的特征,与现代的等高线画法相当接近,比宋以后直到明、清经常采用的人字形画法或山水画中的峰峦那样的画法都要高明。对地形复杂的南岭表现得比较清楚,可以看出,作者已将南岭作为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天然分水岭。但图上的山脉都只画出大致位置,却没有标出山名,连在《楚辞》《山海经》中已有记载,相传为舜陵所在的九嶷山也没有标名。
在九嶷山南画着9个柱状符号,柱后还画有建筑物,旁注“帝舜”二字。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表示主要山峰和高低的不同,因为向东也画了7个柱状符号。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根据《水经·湘水注》,九嶷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这座建筑物就是舜庙,九个柱状符号是舜庙前的九块石碑。将著名建筑物夸大地画在地图上,是古今地图惯用的手法。
《地形图》除了突出地貌的表示外,水系画得相当详细准确,这可能与当时军事上的需要有关。图上共有大小河流30多条,其中标注了名称的有9条,泠水和深水还加注了水源。图的北端是《水经注》上提到的营阳峡,两岸山势紧逼深水两岸,画得十分逼真醒目。河流用上游细下游粗的曲线表示,注记有一定位置。主区的河流骨架、河系的平面图形、河流流向及主要弯曲、主流与支流的交汇点等,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今地图,有些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主区的河流也有少数画得不很准确,如辇江、贝江间的距离画得过小,参水(今岭东河)画得太短,花江画得太长,泡水、东江上游都应作西北流向。但总的来说,主区部分的准确性是很高的。
《地形图》上的居民点有80多个,分为两级:县级8个,用矩形符号表示;乡里级能辨认出的有74个,用圈形符号表示。名称一律注在符号里。符号有大小之分,可能用以表示该地人口的多少或面积的大小。在营浦(今道县)、南平(今蓝山县)、龁道等县城和一些重要的乡里之间都有道路相通。能够辨认出的道路有20多条,一般是用细直的实线表示,个别地方用虚线表示。
图上的近邻区可分为甲乙两部分,前者指深水流域和舂水上游以及南平县治一带,后者指都庞岭以西在今广西境内的桃阳、观阳二县,湘粤分水岭以南在今广东境内的桂阳县。近邻区虽已不在三号墓主的驻防范围之内,但仍属长沙国范围,所以仅画出县治和一些道路,不画县以下的乡里一级。甲区与主区之间没有什么大山大川的阻隔,因而制图者对这一带的地形还比较了解,对四个县治的位置画得比较准确,只是水系画得较差,有的河流缺画,有的画得太短,有的形状不符。乙区与主区之间隔着都庞岭和湘粤间的分水岭,制图者了解更差,因此,桃阳、观阳二县境内的水系完全不画,桂阳县内的一条河流(即今连江)应该东南注入北江,图上却画成西南流。县治的位置也有很大的误差。
图上的远邻区已经超出了长沙国的范围,是秦末以来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的辖境,因而图上既不画乡里,也不画县治,仅注了“封中”一个地名,海岸不画曲线而成一个半月形,河流全无注记,并且极其粗劣,山脉、道路也完全没有。其中靠近主区部分所画内容还大概有所指,对靠南近海部分,制图者大概除了知道有几条河流南注入海外,已无所知了。在制图者除亲身经历所获得的地理知识之外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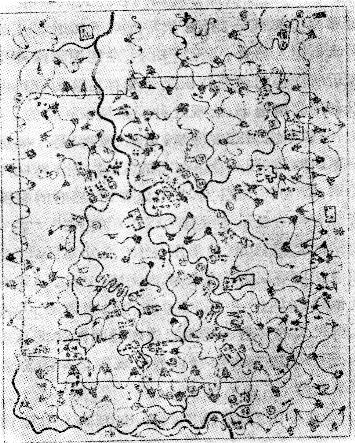
图10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复原图
《驻军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是一幅彩色军用地图(图10)。在图的左、上方分别标注了东、南两个方位。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制图者对方位的表示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方式。本图包括的范围只是《地形图》中的部分地区,即今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潇水流域。主区部分的比例尺约为1∶80000—1∶100000,比《地形图》的比例尺大约一倍。此图的成图时间在汉文帝初年,距今2100多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彩色军事地图。
《驻军图》用黑色单线绘出山脉,有9座山头标注了名称。河流、湖泊用湖蓝色描绘,显示了河道宽狭的区别。在20条河流中有14条标注了名称,主流与支流分辨较准确。守备部队的驻地和军事工程建筑物用黑底套红勾框标出,框的形状、大小不同,可能与地形、驻军多少有关,驻军的名称标注在框内。表示军队行动的道路用红色虚线表示,城堡用红色三角形标示,内注“箭道”二字,居民点用黑色圆圈表示,守备区的分界线则用红色标出。
《驻军图》除了与《地形图》一样绘有山脉、河流、道路、居民点外,突出表示了九支驻军的布防、防区界线、指挥城堡等军事要素,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相当恰当,有关军事的内容表示在第一层平面,而其他要素则表示在第二层平面,主次分明,层次清楚。
毫无疑问,《地形图》和《驻军图》是2100多年前中国测绘技术和地图制作的杰出代表作,是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准。但限于史料,当时的作者是用什么方法和工具进行测绘的,目前还是一个谜。
(三)最早的地图学理论——裴秀的制图六体
裴秀(223—271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从小爱好读书,八岁就能写文章,年轻时才华出众,成为大臣曹爽的幕僚。曹爽败后不久,又受到执掌魏国大权的司马懿、司马昭父子的赏识,曾随司马昭出征。司马炎建立晋朝后,更受到重用,泰始四年(268年)任司空(朝廷最高级官员之一),掌管全国户籍、地图、土地、田亩、赋税等。三年后病死,终年48岁。
裴秀一生最杰出的贡献是绘制地图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他在为《禹贡地域图》作序时提出的“制图六体”(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是中国传统制图理论的重要根据,在西方测绘和制图技术传入中国之前一直起着指导作用。
裴秀的“制图六体”,保存在《晋书·裴秀传》和唐朝编纂的类书《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中。鉴于它的重大影响,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今译〕制图的原则有六条:一是分率(比例尺),是用来分辨范围的大小的。二是准望(方位),是用来确定彼此间的位置关系的。三是道里(道路里程),是用来测定相互间的距离的。四是高下(地势高低),五是方邪(角度),六是迂直(弯曲度),这三方面都要因地制宜,目的是为了正确测定弯曲高低的道路的水平直线距离。如果只有图像而不讲比例尺,那就没有办法区别远近。有了比例尺而不注意方位,那么即使在一个方向画准确了,其他方向必定会出差错。注意了相互的位置而没有具体的道路里程,那么对于在山中或海滨这样的闭塞地点之间,就不可能连接起来。有了具体的道路而不能注意从地势高低、角度和弯曲度三方面加以校正,那么道路的里程必定不符合水平直线距离,也会偏离正确的方位。所以只有参考这六方面的原则,然后才能通过比例尺来确定实际距离,通过方位来确定彼此间的准确关系,通过道路里程来确定相互连接的具体路线,通过对地势高低、角度和弯曲度的测算得出水平直线距离。因而虽然有高山大海的阻隔,边疆异国的巨大差异,地势高低和道路曲折的复杂性,都可以根据这些原则来确定。一旦有了确定方位的办法,那无论道路的曲直、距离的远近,任何地点都不可能定错位置了。
“制图六体”虽然是由裴秀提出的,实际上是此前的制图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是无数制图实践的理论化。从《放马滩地图》、《兆域图》和《马王堆地图》这些现存的地图实物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图者已经成功地运用了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原则。而在西晋以后直到清代的地图制作中,大多数作者更是自觉地运用了“制图六体”。
(四)最早的历史地图集——裴秀的《禹贡地域图》
当泰始四年(268年)裴秀出任司空时,经过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战乱,汉朝留下的地图已经相当有限,而且质量不高,不能满足日常需要。另一方面,在消灭蜀国和吴国的过程中,魏国当局很注意收集两国的地图。尤其是在平定蜀国期间,还专门派遣人员,随军队对沿途的地形、地势、山脉、河流、道路进行调查,然后在地图上核对修改。因而当时已经积累了不少地理资料和原始地图,为编绘新的高质量地图创造了条件。
由于地图所绘的内容越来越多,又不采用适当的比例尺,所以全国性的地图越绘越大,当时的一幅“天下大图”竟用了80匹缣(双丝的细绢),不仅查阅不便,而且也不精确。裴秀采用“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将这幅巨型地图缩小到一丈见方的“方丈图”。但图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备载名山都邑”。由于采用了适当的比例尺,真实感很强,使查阅的人“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
裴秀鉴于自先秦以来,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在古代的地理书《禹贡》中的山川地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后代的学者往往任意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引证,内容越来越混乱,错误百出,因此他根据文献资料作了严密考证。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对有疑问的地点一律不收,凡当时已经不存在的古代地名也都注在相应的位置。就这样,裴秀绘制成了18篇《禹贡地域图》。
《禹贡地域图》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历史地图集,也是目前所知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图集所覆盖的年代上起《禹贡》时代,下至西晋初年,内容则包括从古代的九州直到西晋的十六州,州以下的郡、国、县、邑及它们间的界线,古国及历史上重大政治活动的发生地,水陆交通路线等,还包括山脉、山岭、海洋、河流、平原、湖泊、沼泽等自然地理要素。从图集分为18篇以及以后的历史地图集的编排方式来推测,这部图集很可能是采取以时期分幅和以主题分幅两种方法,即以时间为序绘制不同时期的疆域政区沿革图,又按山、水或其他类型绘成不同的专题图。
由于西晋统一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十六国和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和战乱使地图很难得到保存和流传,所以《禹贡地域图》不久就失传了。但7世纪初隋朝的建筑学家宇文恺曾提到裴秀的“舆图”采用“二寸为千里”(大致1∶9000000)的比例尺,这“舆图”很可能就是《禹贡地域图》的残卷。但此后就再也未见到关于《禹贡地域图》流传的记载了。
(五)京相璠、杜预、谢庄的成就
关于京相璠其人,现在能够了解的情况已经很少。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和《隋书·经籍志》的几条材料可以证明:他是西晋初(公元3世纪中叶)人,是裴秀的门客,曾协助裴秀编绘《晋舆地图》,并且著有《春秋土地名》三卷。
《春秋土地名》原书早已散失,但清朝人王谟所辑《汉唐地理书钞》中收集到90条,其中为郦道元《水经注》中所引用的材料最多,有人统计共有70多条(其中,济水、瓠子河各12条,颍水6条,沁水、洛水各5条,阴沟水、泗水、沐水各4条,汝水、淮水、谷水各2条,沔水2条,河水、![]() 水、清水、涑水、易水、誆水、渭水、丹水等各1条)。这既可以说明郦道元对京相璠这本书的重视,也能证明京相璠不愧为一位地理知识渊博、治学态度严谨的学者。
水、清水、涑水、易水、誆水、渭水、丹水等各1条)。这既可以说明郦道元对京相璠这本书的重视,也能证明京相璠不愧为一位地理知识渊博、治学态度严谨的学者。
毫无疑问,京相璠的地理学成就必然在帮助裴秀绘制地图的过程中得到发挥和应用,我们在高度评价裴秀在中国地图史上的地位时,不应该无视京相璠的贡献。
据《晋书·杜预传》记载,杜预长期潜心钻研《左传》,自称有“《左传》癖”,在著成《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同时,晚年还编绘有《盟会图》,时间应在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后不久。顾名思义,《盟会图》所表示的是春秋时代各国诸侯举行盟会一类政治活动地点,应该是一种专题历史地图。此图以后未见流传,由于资料太少,我们还无法推测此图的其他情况。
大约在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稍前,当时担任随王后军谘议兼记室(参谋兼秘书)的谢庄制成了一种“木方丈图”,用来表示《左传》中所记载的春秋各国的“山川土地”。有关此图的具体情况,只有《宋书》卷八十五《谢庄传》中的几句话:“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县殊,合之则宇内为一。”据此推断,这是一种拼板地图,以每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范围为一块,上面画着山川、城邑等内容,将每一散块拼合起来,就成为一幅方一丈左右的木板全图。至于每一块是否还制成立体,从原始记载看是无法肯定的,一些论著把谢庄的“木方丈图”作为立体地形图的雏形尚缺乏根据。
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南方,山水画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主要流派。山水画虽也有写实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表达作者的意境和感情,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忠实记录。即使是写实性的山水画,作者一般也都有固定的视角,因远近而有大小、疏密的差别。山水画的盛行逐渐影响到地图的绘制,形成了一种山水画形式的地图。这种地图基本上采用直观描绘的方法,比较注重表示对象的具体形状,如山峰的岖崎、河流的弯曲、建筑物的外表等,对方位、距离、比例尺这些对地图来说更重要的因素却不重视,甚至完全不考虑。图上内容的选择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作者熟悉的就多画,不了解的就少画,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成比例关系。从地图绘制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种山水画式地图的出现是一种倒退,由此而产生的大量地图比起早期的《放马滩地图》《马王堆地图》和裴秀绘制的地图来都有很大的退步。但这种地图比较直观,既容易绘制,又能为大多数非专业人员所接受,所以长盛不衰,构成了中国古代地图的大部分。直到清代,一般方志和书籍中所附的地图还是这样一类写意山水画式的。
有关葛剑雄文集①普天之下的文章

对各级行政区的图经编纂和地图的绘制,唐朝政府已有明确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朝廷定期编绘全国性的地图。唐代疆域辽阔,中原与边疆地区、唐朝与境外各国间的往来交流极其频繁,因而比较注意地理资料的积累和地图的编绘。有机会到外国的使臣、将领,巡视边疆地区的官员还主动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绘成地图。......
2023-11-30

透过传说的神秘色彩,我们还是不难想象这种铸在鼎上的图画的真相:这实际上是铸在鼎上的原始地图。由于这九只鼎上分别铸有全国各地的山川和珍奇物产的图形,因而被当作拥有九州全权的象征。先民将原始地图铸在铜鼎上,或许正是出于使它们能够长期保存的考虑。......
2023-11-30

到托勒密时代,西方古代的科学制图学达到了高峰。令人遗憾的是,托勒密时代所绘制的地图,没有一张能够流传下来。圆的上部是亚洲,几乎占了世界的一半。......
2023-11-30

当我们最终站在壶口瀑布前,在震荡山谷的喧腾水声中仰望倾泻下来的黄河之水时,就再也不会怀疑诗人是过分夸张。这就得从我们的祖先探寻黄河之源说起。(一)导河积石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之一《尚书·禹贡》中有一部分内容称为“导水”。......
2023-11-30

它“预言”过去简直像记录历史一样正确,而对未来也讲得不留余地,连“可能”一类不太肯定的词语也不用。总之,他们不愿意接受“世界末日”的预言,却关注着自己的明天,并且希望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
2023-11-30

因为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关于黄河清浊的证据,就是《左传·哀公八年》引用的两句佚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要等到黄河变清,一个人能活多久?人们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已经肯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黄河是不可能变清的,所以才会发出如此毫无信心的慨叹。天长日久,河床不断抬高,逐渐成为高于两岸地面的悬河。......
2023-11-30

六、天外来客——来自地球外的威胁天空一向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大概每个民族都有对天空的崇拜和向往,他们心目中的神灵大多生活在天上,肉体或灵魂升天自然成为一种最高的追求。降落在宋国的五块陨石并非那次天外来客的全部,因为陨石在地球大气层高压带降落时受到高温高压气流的冲击,有的陨石会发生爆裂,变为许多陨石碎块落向地面,这种现象被称为陨石雨。......
2023-11-30

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到了秦汉时代,秦、楚等国的旧地都成了统一国家的一部分,渭河流域的关中盆地还成了首都所在,这些地区当然都算中国了。中国往往被作为中原、中心地区或先进地区的代名词,广义的中国又是中原王朝的代名词。......
2023-11-3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