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虎丘山塘,萧然敝庐中悬思陵御书,时肃衣冠再拜欷歔太息。汧长子,少有才名,年二十一举崇祯壬午乡试。[63]文中以“六一居士”作比,是为衬托和赞誉一竹斋主人与“六一”之义一样的高逸旷达的“一竹”之情。......
2025-09-30
5.3.2 差异点
文征明画中的世俗气体现在他对南方园林的实景和详尽的描述上,真赏斋中的景物虽然在文征明的笔下已经经过了高度的简化和提炼,但是在描绘手法上仍采用了详尽细腻的细笔实笔,从斋室到古木、湖石甚至到斋背后的竹林,都似乎未作任何随意放松的处理,笔笔都在细致勾画;而且画面内容极为饱满多样,在景物的数量和复杂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一竹斋图》;同时由于对界画技法的接受和吸纳,文征明在屋宇的造型和一应俱全的屋内陈设的设计和刻画上都破费心力,他的注意力似乎完全被那些名士斋中雕梁画栋的建筑装饰和精雅绝伦的古玩玉器给吸引了,有非刻画出不可的意愿和耐心,而这样的举动更需要充足的时间和平和且略微慵懒的心绪的依托,明代中期那种相对安逸、富足的环境滋生和助长了这样的心绪,为创作出具有浓郁世俗生活气息的文人斋室画提供了条件,它带给人更多的感受是那种远离尘嚣却又能更好地热爱和享受生活的精神态度。
因此在文征明笔下出现的斋室主人各个都是精神愉悦的,虽然幽居独处却没有丝毫哀伤和自怜的痕迹,如《真赏斋图》中所画的主人华夏,在现实中他正是因为被罢官免职才回乡建起了这处真赏斋别墅,按理说在内心中应该是愤懑不平的,但文征明却把他画成了一位幽居自适、交朋结友无不快活的人,这样的刻画透露着现实中的人物心境,华夏终究未能在官场的不如意中消沉,他在鉴赏中找到了他人生中的大乐趣,这样乐观的态度感染了他的好友并又被其忠实准确地表现在了画中,华夏的隐逸之情是充满着对世俗眷顾,而没有无可化解的人生痛苦的中隐之志,因此这种恬淡悠然的轻快感便从画卷中清晰地传达了出来。这些特点形成了文征明画中的世俗气,这种世俗气又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和享受的态度。
这种醇厚、实感、繁缛细碎的描绘手法在恽寿平的画中是不可能找到的,这点正是源于他的时代和他的人生,对于一个面对残峻生活的遗民画家来说,他无法获得那种殷实且无忧的和平年代的生活体验,更无从在其画作中展现和表达这种生活场景。于是在恽寿平的画中,没有穷尽功力描画不休的细笔、实笔,唯有主题的墨竹的形质做到了清晰工致,其余部分皆以虚淡之笔描绘。他以极为简约松动的笔触构建起了画中的斋舍,屋内没有文征明笔下繁琐的陈设,除过对门而坐的斋主人和一尊香炉别无他物,线条简洁到只用了几根长线,圆转数笔便勾画出了主人的形体,为了更求简洁疏朗,斋主人的面部亦被留空未画,真是简到了惜墨如金的程度;屋外的山石树木用笔更为虚透轻盈,淡赭墨寥寥数笔,勾画出散散落落的荒寒幽寂的林木景象,相较于文征明画中树木和湖石的形状乖张,且具有的沉甸甸的厚重感来说,恽寿平画中的树木、山石真是到了不能再虚灵轻透的程度,且形状均是朴素含蓄,使得人看不到张扬的世俗趣味干扰过的痕迹,有一种真正远离尘嚣的冷静、孤迥和飘逸之感。这些特点不仅出现在恽寿平的画作中,更在他同时代的画家作品中体现出来,简约、清逸对世俗生活的不感兴趣的隐逸情感,成为他们绘画的主旋律。因此这种紧跟时代的笔墨手法透露了时代的精神和内涵,恽寿平的《一竹斋图》带有着清晰的清初绘画特色。
其次,两位画家通过各自不同的表现手法展示出画中人物迥异的精神状态,《真赏斋图》是以一种叙事的方式展现斋室主人的富足、丰富的生活场景;而《一竹斋图》中则以隐士孤坐的手法来表达冷峻孤独的遗民情怀。
这种无剧情的隐者孤坐的表现手法在恽寿平的其他斋室图中也能经常看到,如他50岁流寓娄东时为当地的遗老隐士荣峰所画的一幅《林居高士图》(见图7),画中亦是在山间有一椽茅屋,屋内孤单地坐着一位抚琴面山的隐士,周围萧瑟静寂的自然环境和人物淡定无声的状态,衬托出一种冷逸清醒的人与自然对话,“人神之交”的感觉和场景,为了补充表达这种心境,恽寿平在此画中题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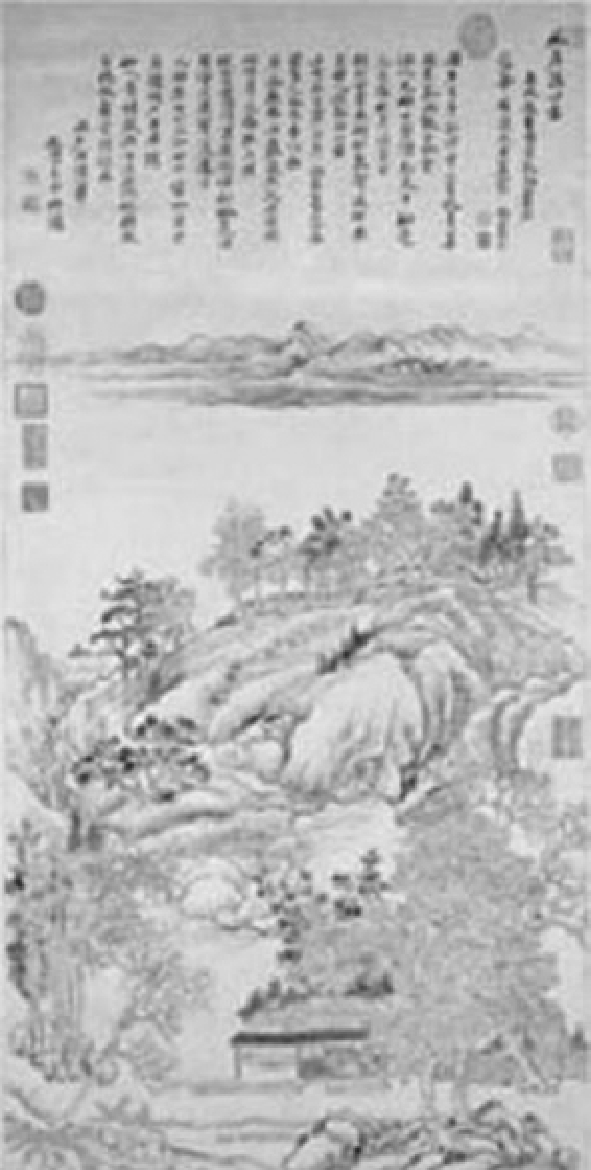
图7 清恽寿平《林居高士图》轴,纸本,淡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https://www.chuimin.cn)
草木本无性,岩泉亦沉溟。借问此何年,天醉殊未醒。人间无西山,不向山中宿。吟诗猿鸟趋,闭户日月独。[18]
天地自然那种恒常不居的“无情”就在这种万籁息声的冥想中被感悟,坚守清志的人是孤独的,而处身于流转不息不为所动的自然中,这种孤独感就愈发的强烈,因此恽寿平才慨叹道:“世间连伯夷叔齐隐居的西山都找不到了!”其实西山还是可以找得到的,但现实中那种能够欣赏伯夷叔齐的人却找不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种凄凉无依的语气无疑是在暗示现实社会所带给他精神上那种巨大的压抑和孤独感。
同时,在人物形象和衣着的刻画上,两位画家更产生了微妙却意蕴深刻的反差,这种反差我们亦可称其为人物形象感的“实”与“虚”的表现手法,通过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反映出的是二者内心中明显异趣的隐逸精神的不同。如文征明的画中,斋室主人和客人甚至家童的着装均为典型的明人特征,身形比例合理,面部刻画精准,文征明在这里毫无虚构和篡改的意思,他忠实地反映出明代人物现实中的原貌,可以说他是活在时代中又将目光投注于当下的画家,他的艺术充满了现实主义的色彩,他的作品亦没有虚无缥缈的幻觉感和完全凭借想象的臆造,而是将真切还原生活作为最重要的事,这也便是他画中“实”的体现。
而在恽寿平的《一竹斋图》中,虽然人物数量只有一个,而且刻画的极为简洁,但从中仍似乎可以窥测出一种主观表达的意识来,画中的斋主人席地而坐于一个蒲团之上,右侧靠在一个本应于汉代、魏晋时期才常用到的三足凭几上,着装的样式也非常类似于汉代的装束。这样的一种非真实描绘和时空错乱的表现,一定会使得那些完全不谙画作信息的人在初次观赏此画时便无法将其与清代这样一个时期建立起联系,画中斋主人已经不是现实中人物的再现,而是画家主观臆造的产物,是画中“虚”的意味的体现,带着更多的对于现实的回避和遗忘;但他的这种虚构又带出了另外的一种真实性,即内在精神形象的真实反映。在清初,文人对于现实政权的抗拒是决绝的,他们宁愿幽隐林泉,独坐孤峰,放弃一生的政治抱负和安稳生活也不愿做背宗忘祖的人,所以他们的遁世隐居是彻底的出世和被世所遗弃。同是追求隐逸,明人则将更多的精力和兴趣花费在了叠山理水,筑造园林的过程中,因此这种隐逸建立在调节生活附庸风雅的情趣基点上;而清人的隐逸是在与时代的斗争,以及与自己思想的苦闷对话中进行的,他们的生活极为清贫凄苦,需要付出巨大持久的毅力和决心,因此他们在精神境界上是无法在现实中甚至前代中找到共鸣和寄托,而与他们时代境遇相通的魏晋时期的隐逸思想才是他们真正向往的精神家园。因此无论是斋室主人唐宇肩,还是画家恽寿平,或是《一竹斋图》卷画后的遗民题跋者们,他们内心的境界是暗合古代的隐逸精神,恽寿平表现出这一理想,便创造出了这样一位具有魏晋时期形态的斋室主人,他以虚构的手法还原了束缚在清代社会外衣下的追求魏晋隐逸思想的文人精神的形象和内涵。
因此从这里,恽寿平在画中所寄予的思想深度便可见一斑,他和文征明画中人物真实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截然的反差。
从两幅画作的时代风格中可以发觉,尽管明中与清初文化一脉传承、相距不远,但恽寿平却并未能在明代画家的时代风格中找到可以共鸣的精神内涵,明人那种温和、安定的静逸感是无法表现和达到恽寿平对于人生尖锐冷峻思考的深度的,于是他将目光跳离开明人,投注到与他思想共通的元人那里,找寻合乎时代精神的更为有力的笔墨表现形式和意境感。
相关文章

居虎丘山塘,萧然敝庐中悬思陵御书,时肃衣冠再拜欷歔太息。汧长子,少有才名,年二十一举崇祯壬午乡试。[63]文中以“六一居士”作比,是为衬托和赞誉一竹斋主人与“六一”之义一样的高逸旷达的“一竹”之情。......
2025-09-30

5.1关于斋室题材画作的定义“斋室画”,这个名词的运用曾见于我国台湾学者邱士华的王蒙《芝兰室图》研究一文中,而与“斋室画”同义、相近的名词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也很多样,如“书斋山水”一词,首见于何惠鉴的《元代文人画序说》一文,其中他将元代斋室题材画作称为“书斋山水”[1],他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对于元代文人画家的活动场所和活动内涵的考虑而拟定的名词。......
2025-09-30

[27]壶公钱杜在这幅《一竹斋图》卷中留下了多处的鉴藏印痕,一处是出现在题额、画面中,以及画后二曲先生李颙跋中的“壶中墨缘”朱文方印,另一处是出现在画面中左下角的一款“壶公心赏”朱文方印。......
2025-09-30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这幅产生于清代的斋室画的风格特征,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找到更为确切的答案和定位,以《一竹斋图》的斋室题材这个点出发,延展开来的相同题材画作的历史追溯和比较工作,似乎成为一条非常必要且可行的探寻线索和手段。从《真赏斋图》到《一竹斋图》,我们也许能够获得明清斋室画“时代风格”的演变态势和过程。......
2025-09-30

《一竹斋图》卷中,今释和尚为“一竹斋”的题诗为:赚煞王家痴子猷,眼光如雪又迷真。[23]因此,文人、画家常有以“龙公”来比喻仙山之竹的寓意。[25]今释和尚用“龙公”和“鹅溪千尺”来表明仙境之物非实有,真正的好竹在绢素之上,其意亦有赞喻画中之竹的妙感超逸的意思。......
2025-09-30

2.3一竹斋主人与“一竹”精神首先,很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位一竹斋主人唐宇肩,其又名予坚,字若营,号无营散人,江苏常州武进人,是明末著名文学家、抗倭名臣唐顺之的裔孙,唐宇昭的族弟,和恽寿平亦同里,清初的著名学者、书法家,曾为明末孝廉(举人),入清不仕,《江南通志》中称其:性孝,善书法,家贫卖字以供甘旨,与郡中恽格画并珍于时。......
2025-09-30

0.2.1选题中研究方法的参照选择具体的作品来作为研究一位画家和时代的切入点的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在中国老一辈学者的研究中也有运用,但这种方法更多更早则见于西方学者的文中,对于一位画家的笔墨特征和时代风格,相较于宏观、空泛、笼统的理论概括和抽象总结,西方学者更为注重的是一种“让事实说话”的方式,即通过画面结构、技法特征、笔墨符号等因素所传达出的实证依据,并通过与其他画家的纵、横时代的比对的考察手法......
2025-09-30
相关推荐